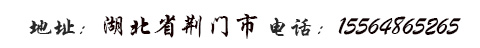建筑学社从木构源流到空间特征交织于史
|
FromtheOriginofTimberStructuretoSpatialFeature ——DoubleConjecturebasedonPerspectiveofArchitectureandHistory 关键词:梁优先;柱优先;盒子空间;空间连续性Keywords:BeamPriority;ColumnPriority;Box-shapeSpace;ContinuityofSpace 1日本木构与现代空间 1.1打破“盒子” 西方的建筑布局,从现代主义开始走向自由。年,在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首的现代主义巨匠们的努力下,“空间”的概念被写进了《雅典宪章》,“传统盒子的解体”与“空间连续性”其实是同一描述的一体两面,前者描述了操作的机制和它所颠覆的传统,后者则描述了现代主义建筑空间要达成的效果。 “盒子”是西方的传统,它基于至迟自迈锡尼以来就在欧洲占主流地位的砖石砌筑技术。 这样的建筑通常是墙体承重的——要想做成石头框架,就不得不尽可能缩小柱距,在大规模建筑中,柱阵必然是林立的,就如波斯的“百柱殿”那样,空间也很难谈得上自由。墙体承重让建筑自然而然的呈现出有如方盒子的封闭格局。 而在对屋顶的构建上,基于砖石就只有起拱一条路——事实上,古希腊神庙的石头楣梁体系的屋顶都是木梁架。拱结构需要把侧推力传递给厚重的墙体,所以在建筑体量上,拱顶必然与墙体紧密结合,空间的尺度和形态也因而受限于拱顶的跨度规模。 综上,作为西方传统的砌筑技术所必然形成的“盒子”一直绑架着建筑的布局,这样的束缚一直到诸如钢和混凝土等支持框架结构的新材料的出现。 1.凤凰殿与桂离宫 西方建筑学传统对框架结构缺乏准备,直到年芝加哥世博会上日本凤凰殿(图1)的横空出世。在日本发展了上千年的木构技术对西方建筑世界的冲击是立竿见影的,同年,赖特的草原别墅问世:温斯洛住宅的屋顶坡面平缓,明显有别于典型西方木构中陡峭的人字形屋架;入口开在“檐面”,与赖特橡树山庄的自宅中“山面”开门的做法恰成对照,这是小规模建筑摆脱了屋架落脚处的承重墙才会有的做法;在屋顶与围护的交接段,赖特用沙利文式的面砖饰面明确区分了两者,这显然来自凤凰殿结构中铺作层对屋顶与围护的分隔所带来的外观表现(图)。上述这些特征让赖特的草原别墅显得别具一格,并迅速风靡西方世界。 ↑图1:年芝加哥世博会日本凤凰殿 ↑图:温斯洛住宅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凤凰殿的启示改造了赖特建筑的外观,却并没有导致赖特从根本上变革建筑的内部空间;另一方面,赖特对建筑外观的“凤凰殿化”改造,也并没有令草原别墅打上鲜明的可识别的东方烙印。矶崎新在赖特的东京帝国饭店设计渊源的考证中,也注意到了凤凰殿的抬梁体系与西方建筑传统的相似性,他在《建築における「日本的なもの」》(《建筑中的“日本的”》)一书中指出: “帝国饭店的基本构成,是将基本功能空间诸如大厅、主要食堂和礼堂置于轴线上,而住宿的卧房次第排在两翼。这样的布置是基于西方公共建筑的基本形式,承袭自帕拉第奥。但是,类似的布置也可见于东京平等院凤凰殿,赖特肯定是在借鉴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的那个复制品,正是那次世博会让赖特迷上了日本。”[1]15 显然,凤凰殿式的结构并未直接导致空间的自由化,真正让现代主义的巨匠们释放空间的,是他们沿着凤凰殿的踪迹造访日本时所领略的桂离宫的风采。桂离宫的空间是自由连通的,建筑师们在这里看不到“盒子”,却体验了“空间的连续性”。那段时间,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员们甚至痴迷于日本推拉扇的“自由隔断”,如密斯·凡·德·罗在威森霍夫的设计,以及里特维尔德著名的施罗德住宅,都表达着对空间连续性的强烈渴望。而作为同类尝试最卓越的成果,赖特的“流动空间”如今已经成了现代主义的重要遗产。 对中国而言,日本的建筑传统是源自中国的,赖特演讲中对《老子》章句的引用则一直是中国建筑学坚信本土传统优越性的一针“强心剂”。但这样的关联太过宏观和粗暴了,如上文所呈现的,即便同属日本建筑传统,凤凰殿与桂离宫的特征及其影响也如此明显的不同。因此,中国传统木构的源流及其影响,也需要我们格外细致的观察和研究。 木构逻辑 .1抬梁与穿斗 中国传统木构按构成方式主要可分“抬梁式”和“穿斗式”两大体系。至迟从隋、唐时代起,抬梁式开始成为中国木构的主流,成为主要官式、纪念性建筑的常规模式,中国现存的古代经典木构绝大多数都是抬梁式的。与此相应的,穿斗式木构在中国逐渐边缘化;但不可忽视的是,穿斗体系从长江流域传至日本并在那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以桂离宫为代表的“书院造”木构中臻于巅峰——那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空间原型。 穿斗式木构(图3)的基本逻辑很简单:先树立柱子,然后用称为“穿枋”或“穿”[8]56的细木件将柱子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一榀框架单元;屋顶骨架则直接架在柱顶,屋面造坡由柱的高差来实现。严格来讲,穿斗式木构中是没有典型意义上的承重梁的,屋顶荷载直接施加于柱子,而穿枋则仅起拉接作用,以传递水平荷载并保障构架的整体性。总之,穿斗式木构的核心特征是柱子,空间形态也是由柱塑造的,构架逻辑可以概括为“柱优先”,其跨度有限,但构成模式非常灵活。 ↑图3:穿斗式木构逻辑 抬梁式木构(图4)顾名思义,是有梁的,它在柱顶架设一套梁架,这套梁架通常是由多层梁叠合而成,如此构成一榀基本的框架单元,作为屋顶骨架的檩条则搭在各层梁端以传递屋面荷载并实现屋面造坡。由于抬梁式构架中梁架系统与柱网系统是各自独立的,我们甚至可以把整套梁架完整的从柱网上“端”下来——这样一来不难发现,决定抬梁式木构特征的是它的梁架系统,建筑形态也是由梁塑造的,而柱网仅起支撑作用。因此,与穿斗式相对,抬梁式木构是“梁优先”的。在“梁优先”的模式下,柱不与屋顶发生关系,位置相对自由,于是才可能出现流行于金、元两代的“移柱造”和“减柱造”,可以实现很大的跨度,但梁架的灵活性不高。 ↑图4:抬梁式木构逻辑 从木材先天的杆件特性出发,木构在出现之始应该更接近立柱加上人字形屋架的构成,优先令杆件轴向受力——就如洛吉耶在关于建筑起源的图示(图5)中描绘的那样,应该是“柱优先”的。而李允鉌先生在《华夏意匠》中也指出穿斗式木构早于抬梁式[]05。可以认为,如果仅贯彻木构自身的发展逻辑,木构之主流应该是穿斗式的。后续的追问也就变得更加有趣:抬梁式木构中那些发达的横构(包括梁和斗栱)真的如李允鉌推测的来自对穿斗构架的“减柱”么(图6)?抬梁式木构是否完全由木构逻辑自身的演变而成?为什么抬梁木构兴盛于木材资源匮乏的黄河流域呢?为什么能支持更大建筑规模的抬梁结构没有在木材资源更丰富的长江流域发展起来呢? ↑图5:洛吉耶《论建筑》中的插图 ↑图6:李允鉌认为抬梁式木构来自穿斗式木构的减柱 .铺作层 斗栱是中国传统木构中最独特的要素。它的工作原理有若天平,利用杠杆原理平衡两端的荷载,以缩短梁的计算长度,提供更大的跨度和悬挑深度(图7)。当斗栱多层叠加,也相当于通过叠垒增加了拱身的高度,增强强度。必须指出的是:斗拱叠加后,越靠上层拱身越长,同时也扩大了交接面,可以视为被放大的交接节点;而多组斗栱连成片,也就构成了交接能力异常强大的“转换层”——即所谓“铺作层”。 ↑图7:斗栱 典型古代木构上的铺作层通常居于柱与梁架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层,进一步连接——也可以认为是进一步分断了柱网层与梁架层。(图8)这样的结构层次不可能在“柱优先”的穿斗式构架体系中发展起来,而是要基于抬梁式木构的“梁优先”前提。所以,斗栱在以抬梁式木构为主流的中国大陆得到长足的发展,即便在斗栱开始丧失结构意义的明、清木构中,铺作层仍然作为装饰要素顽强的留存于建筑之上,甚至在规模和工艺上更加繁复和精巧。 ↑图8:抬梁式木构中的铺作层 相比之下,斗栱在日本的境遇却总略显“发育不良”——日本木构的发展是围绕着穿斗式展开的。根据松尾佐助的人类学研究,日本文化从属于发源自中国云南、经长江流域末梢划过日本冲绳的“照叶林文化带”,长江流域的木构技术伴随着水稻、吃茶及月亮崇拜等文化一道传入日本。尽管南方的穿斗式木构传统在中国本土已经没落了,但在日本却星火相传。张十庆认为日本木构从法隆寺的时代起横架就很薄弱,[6]47而张毅捷则在《中日楼阁式木塔比较研究》中进一步指出:日本历史时期建筑结构的发展并非“横架”的不断加强。[3]甚至,桃山时期日本匠作典籍《匠明》中竟没有关于梁的论述。因而在日本木构发展的各个阶段,斗栱总是在从大陆(即中国)传入日本时比较发达,而在“和化”的过程中退化,例如在自宋传入的“禅宗样”到日本本土化的“和样”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那样(图9)。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斗栱在许多日本历史建筑中都有出现,但其规模能构成“铺作层”的却并不多,诸如法隆寺、唐招提寺等有典型铺作层的木构,都是比较纯正的中国式样。所以,给西方现代主义带来不同影响的凤凰殿和桂离宫,其实分别反映了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木构发展方向。 ↑图9:禅宗样与和样构架的比较 作为结构转换层,应用于楼阁建筑的铺作层更能昭示其结构逻辑。木材不像砖石那样能无限叠加,木构构件的尺度受限于木材的尺度,要实现大规模的楼阁,在高度上保证“柱优先”是很难的。中国的楼阁从汉代起就通过铺作层抬梁来实现层间的转换;到辽代的佛宫寺释迦塔臻于巅峰,九层塔中有四层是铺作层(图10),在铺作层的转换下,每层结构可以各自为政,所谓“叉柱造”(图11)就是各层柱位错开的做法。这样的“抬层”结构是对“抬梁”模式更极致的演绎。 ↑图10:应县木塔剖面图 ↑图11:叉柱造 相比之下,日本经典的五重塔(图1)尽管外观上是楼阁式的,其结构却并非在空间上“抬层”,而是在塔内树立巨大的“心柱”(中国称“刹柱”),外层构架貌似抬梁式交接,层间转换却是由斜向的下昂和椽子来完成的;其横架全部插入心柱。这样的结构有鲜明的“柱优先”倾向,那些栱尾的横构与其说是“梁”,不如说是“穿”。为此,日本的塔很难达到如释迦塔的规模。 ↑图1:五重塔的结构剖面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类木构发生了各种各样微妙的互相借鉴与形式交融,在许多建筑实例中——尤其是在日本——我们都无法泾渭分明的区分它们。而木构中的铺作层则恰似一把尺子,可以度量木构的源流逻辑。铺作层不仅实现了柱网与梁架、楼层与楼层的交接,许多唐宋时代建筑题材的界画中都显示,铺作层甚至可以作为建筑与台基的交接(图13)。铺作层可以衔接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结构——它会是由木构体系自身发育而成的么?它会不会是繁衍自木构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媾和呢? ↑图13:李昇(五代)岳阳楼图 3木构源流 3.1从盘龙城土墙到夯土高台 在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商代宫殿遗址中,就表现了一种不同结构体系间的质朴媾和:以一组四开间的土墙“盒子”为基础,其上横跨木梁架以构成屋顶,其四周则外接木构形成柱廊。宫殿复原图的横剖面(图14)与典型抬梁式木构的横剖面非常相似。 ↑图14: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宫室遗址复原图 首先看屋顶,当墙体解决了竖向支撑的问题,那么木构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实现跨度并构建屋面坡度。在这样的关系下,木构系统自然向“梁优先”的横向发展。两河流域就在一组与盘龙城类似的土墙上发展起了水平的密肋体系(图15),其横构的水平性更甚于中国——他们完全不起坡,并最终在平顶上构建了巴比伦空中花园;至今,中国川藏一代石头墙上架设的,也是类似的密梁平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组合中,木构得以明确区分于承重墙,从而作为独立、完整的梁架系统发育起来,也只有在这样鲜明二分的体系下,才会衍生出作为转换结构的“铺作层”来。 ↑图15:两河流域的平顶结构 从这一路径来梳理抬梁式木构的起源,不止解释了有悖于杆件逻辑的叠梁构造和铺作层问题,也回答了上文提出的抬梁式木构何以兴盛于北方的疑问——启动它的是土墙,而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恰将北方文化归结于黄土地带的馈赠。所以,我们只需将那组土墙置换成两排柱子,抬梁式木构就赫然现出端倪了——如建筑史家维特科威尔所云:“墙断裂成为柱,是建筑学的一件大事”——抬梁式木构体系中均一的柱高其实是继承了墙的特征。 再看看四周外接的木构柱廊,它与土墙交接的方式并不是“抬”而是“穿”。这一圈柱廊不止提供了一层“灰空间”,也在外观上为建筑提供了完整的木构外皮——这很可能就是“副阶周匝”的起源。 正是这种在“土盒子”上附着木构架的策略,令原本轻灵的木结构获得了实现纪念性表现的机会。最雄辩的写照是秦汉时期的高台建筑。无论是秦王宫还是汉代明堂都沿袭着相同的做法(图16):以一个巨大的夯土方台为基础;其顶部建严整的大屋顶木构建筑;其四周环以木构回廊——这也可以视为“重檐”做法的肇源。从策略上,夯土台与盘龙城的土墙异曲同工,而汉末夯土的退出,其实伴随着柱网取代夯土实体从而提空内部空间的诉求,盘龙城土墙与明堂土台的差别,也就成了“双槽”与“金厢斗底槽”(图17)的差别。 ↑图16:秦王宫剖面图 ↑图17:双槽与金厢斗底槽 其实,从内部空间来看,由于受上部梁架位置的束缚,建筑的形体也同时被决定了。抬梁式木构的纪念性主要是表现在外观体量上的——那正是高台建筑的血统。至于比起南方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民族为何如此强烈的追求纪念性的问题,理论家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中对相关美学问题进行了宏大的人类学论述,本文概不赘述;单就张良皋先生在《匠学七书》中对巢居与穴居传统的对比分析,几乎已经围合出了抬梁木构在北方黄土技术下的演变方向。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其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影响日隆,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佛教石窟也都施加如夯土台外圈的外接的前廊(图18),开间居中的做法更适合信徒从外部朝拜神庙里居中的偶像,奇数开间的内外沟通也从此时起彻底取代了柱子居中从而“分庭抗礼”的内部空间关系,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由外观纪念性所导致的从中柱到开间的转变,同样也发生在古希腊的神庙的演变历程(图19)之中。 ↑图18:麦积山石窟七佛阁(北魏) ↑图19:希腊建筑也经历过中柱时代 再观察一下屋顶的构造,东西方木构逻辑的本质区别在于坡屋面的构成方式不同。西方木构始终受限于人字形屋架的尺度,西方建筑史是由拱券书写的,他们从来没能发展出大型的木构(图0)。而中国木构则很早就放弃了人字形三角屋架,屋面的荷载由檩间的椽子分段承担,这样,屋顶的规模就不再受限于斜屋架的木材尺度,梁架能提供多大的连续跨度,屋面都可以由椽子叠加而成(图1)——在这样的构造下,屋面举折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在抬梁式木构中,建筑的平面规模可摆脱屋面规模的束缚由多跨的柱网来实现;而竖向规模则摆脱了对柱高的依赖,由梁的多层叠垒来实现。 ↑图0:西方基于人字形屋架的木构 ↑图1:中国木构屋顶构造 综上,我们基于对抬梁式木构源流的梳理和假设,得出以下推论: 第一,抬梁式木构源自在承重墙体上架设木构梁架的组合结构体系。 第二,抬梁式木构的表现重点在其外观体量的纪念性。 第三,抬梁式木构受上部严整梁架的约束,其形体往往也呈规则的“盒子”状。 其实抬梁以及斗栱的叠垒方式有点像井干式木构中的叠木垒墙(图),这是否也受墙体承重的影响呢?一个有趣的例子:格罗庇乌斯设计的萨穆菲尔德住宅(图3)也许是这位现代主义大师唯一的木构作品,住宅的结构很接近井干式,在阳台悬挑处甚至出现了极似铺作层的“五跳华栱”及出挑的“蚂蚱头”。 ↑图:抬梁式木构的叠梁有如井干 ↑图3:萨穆菲尔德住宅 3.从天地根元造到桂离宫 “天地根元造”(图4)作为日本建筑史的起点,至今仍控制着多数神社建筑的基本型。“天地根元造”的构架由一根中柱撑住屋脊,两根斜构来承托三角形屋面;在关野贞的日本原始住宅想象图(图5)以及日本早期神社中,这一结构原型只是被柱子从半竖穴中举起来,原本的中柱自然是最高的,结构中没有梁,柱间由“穿”拉接,是典型的“柱优先”的穿斗式木构。以三角形的“山面”作为入口,带中柱的构架,以及发达的屋面斜构,这些都是木构作为杆件体系的“原生态”特征。总体而言,尽管深受中国抬梁木构的影响,许多血统混杂的日本木构已经很难被清晰的区分为抬梁式的或穿斗式的,但日本木构的发展方向仍表现出强烈的“柱优先”倾向。 ↑图4:天地根元造 ↑图5:关野贞的原始住宅想象图 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中柱阻挡了入口,在许多神社中,中柱被拆成两根柱的开间,其上以抬梁式形成“山尖”,形成了介于穿斗与抬梁之间的组合构架,(图6)但总体而言,水平向的横构始终没能发育起来。如上文所述,通长的人字形屋架受材料长度所限,严重制约了屋顶的规模,于是有了如春日大社本殿(图7)以及宇佐神宫本殿(图8)那样多屋顶阵列的做法。在贺茂别雷神社(图9)中,外接一跨以延展屋面檐口的做法则更为常见,宇佐神宫本殿甚至仅在入口开间局部做了同类的延展(图30)。如前文所述,秦汉高台建筑四周的外接木构以及后来进入法式的“副阶周匝”其实都是类似“穿”的做法,这种做法非常灵活。穿斗式木构从内部无法展示雄浑的梁架结构,从外部也提供不了气势磅礴的纪念性,但“柱优先”的模式却让空间构成可以在水平方向自由的接续延展,如八坂神社中自由凹凸的平面形态(图31),是受梁架排布约束的抬梁式木构不容易实现的。 ↑图6:住吉大社本殿立面图 ↑图7:春日大社 ↑图8:宇佐神宫本殿立面图 ↑图9:贺茂别雷神社本殿立面图 ↑图30:宇佐神宫本殿 ↑图31:八坂神社本殿平面图 但是,在这种“柱优先”的构架模式中,没有发达的梁架体系来构造大屋顶,且以八坂神社那样的平面柱位,也很难构架起整齐的梁架系统来。于是,我们在八坂神社的构架(图3)中看到了单层“转换梁”上架设的密集的穿斗式系统——在这里,举起梁架的柱网与构造屋顶的柱网呈现出两套不同的穿斗式结构,而衔接其间的,就只有那一层转换梁而已,横构系统仍未“发育”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那层转换梁也不是完全水平的,两端尚有称为“桔木”的斜构,那与其说是斜梁,不如说是“天地根元造”中屋顶结构的顽强印记。 ↑图3:八坂神社本殿剖面图 同类的穿斗式屋顶构架,在诸如教王护国寺金堂、室生寺金堂、当麻寺本堂(即曼陀罗堂)等日本古建筑中都有广泛的应用。这样,无论建筑的平面和竖向关系是怎样的,穿斗式构架都可以从容的与之衔接,并构架出想要的屋顶形式来。在这些纪念性建筑的实例中,上部穿斗式构架都被吊顶遮掩起来,其室内空间中都架设了看似抬梁式的月梁作为装饰,这说明尽管日本人始终未能完全适应抬梁式木构的逻辑,却对巨大梁架所展示的雄浑的纪念性充满了憧憬。 因此,仔细审视日本的“彻上露明造”所呈现的真实构架就非常有趣了。在净土寺净土堂(图33)的经典九宫格式构架中,内阵的“四天柱”柱高几乎达到外阵十二根柱的两倍,屋面直接与柱顶相接,梁的尺度与抬梁式木构的梁相当,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梁”都非“抬”在柱顶,而是“穿”于柱间的(图34)——如此严整的“盒子”空间原本更适合抬梁,而深谙宋氏木构法则的重源和尚却顽强的维持着“柱优先”的原则,以至于现代建筑家矶崎新在对净土堂的分析中深深为那被梁穿得千疮百孔的巨柱捏一把汗。[1]11更极致的例子是奈良东大寺的南大门(图35),这座建筑有着巨大的重檐屋顶和外观上多达六层出跳的“超级铺作层”,被日本建筑学界认为是日本最具表现力的木构。但是观察内部梁架可知,这仍是一例“柱优先”的木构,平面上成“分心槽”的三排巨柱由六层“穿”拉接在一起,外观上那两组铺作层其实并不能称为“层”,多数斗栱并不与内部梁架贯通来形成杠杆效应,它们更像是悬挑的牛腿一样“穿”在柱身上——这么个“穿”法,倒是跟五重塔的构架关系异曲同工。这两个例子都生动的说明:即便在追求极致纪念性的建筑中,日本匠人仍倾向于以“柱优先”的构架逻辑来模仿抬梁式木构的结构表现,这反映了抬梁式在日本建筑中的微妙处境。 ↑图33:净土堂平面图及梁架图 ↑图34:净土堂剖面图 ↑图35:东大寺南大门 在穿斗式模仿抬梁式的实例中,穿斗式木构在空间形态上的自由性始终被抬梁式木构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式建筑美学禁锢着。与神庙建筑相比,住宅建筑才是穿斗式木构成长的沃土(图36),而住宅建筑在日本的巅峰就是“书院造”的宫殿或贵族府邸。如本院寺飞云阁、二条城“二之丸”(图37)都有着凭借“柱优先”的优势在平面上自由延展而成的空间布局,这些建筑结构并不刻意通过增加跨度营造大容量的内部空间,也没有从外部创造纪念性的大体量,而是通过由推拉扇自由分隔或连通的空间来创造奇异的空间连续性体验。桂离宫(图38)正是诸多“书院造”中的翘楚,自由的柱网构成了许多气质相异却相互贯通的空间;屋顶回归了“天地根元造”的人字形屋架做法,并在一些空间中采用不施吊顶的露明做法(图39),以彰显质朴。同时,那也是日本造园最鼎盛的时期,而在作为日本源流的中国长江流域,木构在江南园林的地形中则被布置得更加离散…… ↑图36:日本住宅是基于穿斗式技术的 ↑图37:二条城二之丸 ↑图38:桂离宫平面图 ↑图39:桂离宫中的露明屋顶 综上,穿斗式木构的特征可归纳如下: 第一,穿斗式木构符合木构原生的框架性特征。 第二,穿斗式木构很难为建筑提供纪念性的表达。 第三,穿斗式木构可以支持空间在平面上自由展开并保持其连续性。 4空间特征 经过了对“梁优先”与“柱优先”两类木构源流的猜测与讨论,再回到《雅典宪章》的空间主张,回到“传统盒子”与“空间连续性”的对立,回到凤凰殿与桂离宫对现代空间的影响,问题会更清晰有序。 首先,“传统盒子”与“空间连续性”的对立,其实是墙体承重体系与框架结构体系的对立。进而,墙体承重只是体系的起点,东西方都有效的在空间中摆脱了墙体的束缚;西方基于墙体承重建立了拱券技术的屋顶结构,在从“筒形拱”到“交叉拱”再到“十字拱”的演进中(图40),空间本身已不再封闭。技术演进让“墙断裂而成为柱”,但无论空间如何开敞,那发源自承重墙的拱券却仍然控制着整个空间的形态,从这一点上,同样肇源自承重墙体系的抬梁木构确实在空间类型上与西方建筑传统有着微妙的亲缘关系——它们都维系着“盒子”空间。而“空间连续性”也不仅是开放性诉求和柱承重的结果,更多是在空间衍生方式上的方法性革命;这是为什么尽管凡·杜斯堡的空间构成(图41)充斥着墙体,却仍吻合现代主义的空间主张。 ↑图40:拱的演变 ↑图41:空间构成 凤凰殿与桂离宫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不同影响,恰恰代表了“传统盒子”与“空间连续性”两个对立命题的宿命纠缠。赖特真的在凤凰殿里看到框架结构的未来了么?为什么凤凰殿仅改造了赖特建筑的外观?陶特、赖特们在桂离宫里又看到了什么呢? 4.1“柱优先”与空间连续性 其实,最早打破了“方盒子”从而实现“空间连续性”的并不是赖特以罗比住宅为代表的“流动空间”,而是他以丹纳住宅(图4)为代表的对建筑平面的自由展开。简单并置一下丹纳住宅与日本书院造建筑的平面图示,渊源已经很雄辩了。柯布西耶将拉罗歇住宅的双拼平面作为他“构图四则”(图43)中的第一则,则是对同一主张的策略性响应。 ↑图4:丹纳住宅平面图 ↑图43:柯布西耶的构图四则 西方空间革命的愿望是由空间演变本身导致的么?这很难溯源。但由钢铁以及混凝土技术的突飞猛进所导致的结构体系变革却似乎是更直接的动因。新技术将方向隐隐的指向了框架体系,但西方建筑传统疏离木结构传统实在太久了,尽管古希腊神庙的形式语言是基于楣梁体系的,但石仿木构的技术现实让木构特征在建筑中完全沦为装饰要素,从结构本身而言,帕提农的石构梁柱与波斯人的拱顶比起来,甚至与相同地域下更早的的迈锡尼拱顶(图44)比起来都相形见绌。年的芝加哥,凤凰殿向现代主义的先驱们呈现的正是对西方而言已经非常遥远的基于木头构建起来的纪念性建筑的蓝本——注意,那仅仅是个起点。 ↑图44:迈锡尼的阿特瑞宝库穹顶 当西方大师们造访桂离宫后,空间革命才真的开始。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柱优先”的视角,重新审视那显得过于宽泛的“框架结构”概念。如果仅以“柱承重”的标准来看,框筒结构、密肋结构、板柱结构、主次梁结构等许多结构体系都符合柱取代墙承重的空间开放性特征;而当我们以柱在空间布置中的“优先级”来评定,就会发现,主次梁结构(无论是混凝土还是钢结构的)最大程度的摆脱了屋顶结构对空间形态的束缚,才是最符合“柱优先”标准的。密肋和板柱结构对柱网的均匀度和方整排布都有更高的要求;而在框架-核心筒结构中,我们几乎看到了高台建筑的高技版了!迪朗的方法(图45)可以轻易将传统建筑统统放进“盒子”范式之中,却很难规范经典的现代建筑空间的类型,就是因为如丹纳住宅的建筑设计,都是从空间在平面图上的延展开始的,从“配置空间”到“点柱网”,最后才是“覆盖屋顶”,在诸多结构体系中,只有主次梁体系才能充分配合这样的思考顺序。受惠于“柱绝对优先”的框架体系,柱网由建筑师在空间设计的过程中决定,结构师则进而确定梁的尺寸——那才是建筑师与结构师恩怨纠葛的战场。 ↑图45:迪朗《建筑简明教程》中的插图 因此,现代主义以来,随着平面上空间关系的“松绑”,现代建筑呈现出更丰富、自由和贯通的空间性——这是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密斯的砖宅(图46)在风格派绘画的引领下让墙体在平面上自由展开,他的墙体逻辑与屋顶完全脱开,而凡·杜斯堡式的分割(图47)又强化了空间之间的贯通关系,尽管是墙体承重而非柱子,仍符合上述“柱优先”所导致的空间特质;而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图48)中八根经典的密斯式柱则完全站在了“柱优先”的对立面,八根严整的十字钢柱完全受控于“盒子状”的矩形屋顶,密斯为它们包上了镀铬的表皮,让它们在空间中坚决的宣誓着屋顶的存在;其实,那与柱位巧妙脱开的风格派的墙,才是密斯驾驭空间摆脱屋顶的“现代”建筑学宣言(图49)。因此,在现代主义空间语境下,我们可以将穿斗式的“柱优先于梁”翻译成“空间优先于屋顶”。 ↑图46:密斯的砖宅 ↑图47:凡-杜斯堡的《俄罗斯舞蹈的韵律》 ↑图48:密斯的德国馆平面图 ↑图49:德国馆中与屋顶系统分离的墙体 所以,“盒子”式的秦汉夯土建筑中,恰是用“空间优先”的外接环廊来弥补夯土台在空间上的缺席。柱廊有着“空间优先”的特性,这在西方建筑学的传统中更为重要,伯鲁乃医院(图50)与伯拉孟特的坦比哀多(图51)都有类似的“副阶周匝”,这些柱廊纵然是砖石构成,却因循着木框架的空间特征,自古就是框架空间对砖石巨构的空间性补偿。“得州骑警”的九宫格空间训练,尽管起自多米诺式的框架结构,但它先天被封闭于“盒子”之中,空间特征中并没有必然的现代性,反而轻易的接应了维特科威尔对帕拉第奥建筑的空间归纳(图5);因此与坦比哀多类似,对九宫格的空间拓展,也是通过外“穿”柱廊来实现的(图53),这些方法都非常古典;而直到空间训练演进到海杜克的“菱形宫”(图54),那空间序列与受控于屋顶的柱网阵列间的45度扭转,才重演了密斯在德国馆中让空间摆脱屋顶的一幕,其空间特征才在根本上触及了“现代性”——这是为什么“菱形宫”从来不需要柱廊来提供空间补偿。 ↑图50:医院 ↑图51:坦比哀多 ↑图5:迪朗的“九宫格” ↑图53:九宫格中的柱廊 ↑图54:菱形宫 与日本穿斗式构架所面临的困境相似,这种“柱优先”的结构模式下,梁系统乃至整个屋顶往往要迁就柱位,从而其自身丧失了实现结构表达的机会。现代主义以前的建筑史中,代表建筑时代特征的几乎都是屋顶;但唯独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尤其是在空间操作最鼎盛的0世纪上半期,屋顶几乎退出了建筑表现的前沿阵地。也许是丹纳住宅的体量(图55)与书院造那“屋顶跟着空间走”的外观过于形似了(图56),赖特在罗比住宅(图57)中将屋顶“改良”成了强烈的水平性构成要素,并用它将原本离散的建筑形体重新整合起来,这种构成式的表现策略经由凡·杜斯堡空间构成的系统化总结之后,几乎成了全世界现代建筑师在自由的空间操作后“挽救”建筑外观的救命稻草。值得玩味的是,在堪称巅峰的流水别墅(图58)里,那水平性的构成要素由覆盖空间的屋顶变成了拓展空间的挑台,这是否也昭示着屋顶在建筑表现上的“战略性撤退”呢? ↑图55:丹纳住宅外观 ↑图56:本院寺飞云阁 ↑图57:罗比住宅 ↑图58:流水别墅 日本建筑用吊顶来回避穿斗式构架在结构表现上的捉襟见肘,这一做法几乎也被现代主义建筑继承了。阿道夫·路斯曾指出:最古老的建筑细部是顶棚——表层饰面比结构更加古老。[7]7密斯的绝大多数作品都用吊顶来遮掩内部梁架的构造关系(图59)——尽管密斯建筑的柱网非常齐整,其梁架也当不至于凌乱。这种屏蔽梁架的做法必然令柱在空间中的表现成为重点(图60),桂离宫自由的推拉扇正是穿行于这样的柱子之间,那也是现代主义大师们在那里获得的第一印象,直到阿尔瓦·阿尔托的梅伊尔卡别墅里,仍然用吊顶和假柱营造着类似的强烈效果(图61)。 ↑图59:密斯的吊顶做法 ↑图60:德国馆屏蔽梁架后的柱表现 ↑图61:梅伊尔卡别墅 有趣的是,当赖特在约翰逊制蜡公司的无梁楼盖间用玻璃管肆意表现屋顶结构(图6)的时候,建筑空间又重新回归了“传统盒子”的模式;那与流水别墅同期完成,一个屋顶结构优先,一个空间优先,各走极端,终难两全。 ↑图6:约翰逊制蜡公司 4.“梁优先”与纪念性 矶崎新如此敏感的注意到凤凰殿(图63)与帕拉第奥的建筑(图64)有着非常相近的空间布置,并指出赖特那座由石砌墙体来实现的东京帝国饭店更多的因袭着西方的传统。经过对抬梁式木构的源流梳理,我们有理由相信:赖特其实并不必在东西方传统间作太艰难的抉择——“梁优先”与“拱顶优先”都会导致“盒子式”的纪念性体量,而两翼及正立面的柱廊则如前文谈到的,是对“盒子”的空间性补偿。矶崎新认为:在日本备受推崇的东大寺南大门,恰恰是由于取消了宋式木构中常用的“副阶周匝”,才得以表现出更纯粹的结构之美,从而获得雄浑的纪念性的;也正是为了获得那样的纪念性,南大门才执着的将“柱优先”的结构逻辑从外部表现为抬梁式木构。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赖特从凤凰殿的抬梁式表现中仅获得了“草原风格”的外观特征(如本文1.所述),但温斯洛住宅的空间和体量却仍然是个“盒子”。 ↑图63:凤凰殿平面图 ↑图64:帕拉第奥的艾莫别墅 那么,现代主义大师们究竟在凤凰殿中看到了什么呢?是抬梁式木构铺作层及梁架中展现出的卓越的结构表现力!只是这种结构表现的震撼随着桂离宫所引发的空间革命被短暂的遗忘了。多年之后,密斯在绝笔之作——德国国家美术馆的设计中终于取消了那用了一辈子的吊顶,坚决的让钢构密肋屋盖来实现匀质均分的结构表现(图65),这是极致到近乎违背结构法则的“梁优先”的操作:建筑空间被彻底提空了,形体完全被屋顶定义,并完全不触及德国馆中“空间连续性”或“流动空间”之类的话题;巨大的外观体量和空间容量提供了纪念性,这种纪念性,在古罗马万神庙中有之,在中国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有之,却很难在“书院造”的错综空间中找到。 ↑图65:德国国家美术馆新馆 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柯布西耶晚期建筑中那些炫目的屋顶表现(图66),是怎样补偿着他在萨伏伊别墅及其以前作品中的纪念性缺憾的;不止密斯最终寻回了曾被他亲手瓦解的“盒子”,赖特更是将他的晚年作品全部封禁在如飞碟般独立封闭的容器(图67)之中。现代主义确实实现了《雅典宪章》中“空间连续性”的理想,但是“传统盒子的解体”真的那么容易吗?《雅典宪章》意识到它是在对抗着一个多么强大的传统了么? ↑图66:昌迪加尔议会大厦 ↑图67:希腊东正教堂 路易斯·康的实践或许更能代表现代主义的后续方向,他“服务空间”支承“被服务空间”的空间主张,先天就意味着支撑体系与屋顶体系的结构异质,这种异质结构的结合几乎回到了盘龙城“承重墙+梁架”的起点,于是康从一开始就专注的在独立、封闭的“盒子”式大空间中表现梁(图68),他的三角锥形密肋(图69)并不必借鉴密斯在国家美术馆中的密肋,因为他们共享着相同的“梁优先”的表现前提,于是也营造了不相上下的纪念性空间。 ↑图68:耶鲁英国艺术中心 ↑图69:耶鲁英国艺术中心三角锥密肋 日本的“书院造”是住宅空间,日本佛寺建筑的表现原型却一直是中国的抬梁木构。值得玩味的是,同样的局面也被镜像到西方,在“传统盒子解体”的那些年,现代主义建筑的前沿阵地是住宅和展馆,却从未涌现出顶尖的教堂。而当密斯、柯布西耶们寻回了那“盒子”中的纪念性,如朗香教堂的神庙应运而生;路易斯·康那未建成的胡瓦犹太人教堂(图70),在严整封闭的“盒子”中营造静谧之光,令多少后人魂牵梦萦;安藤忠雄更是在他的光之教堂的“盒子”空间中放了两个球,以致敬万神庙的神迹…… ↑图70:胡瓦犹太教堂 沿着“梁优先”的抬梁式木构传统回溯,我们很难回到日本,却必须着眼中国——这不正是中国建筑师梦寐以求的境界?有趣的是,在“梁优先”的视角下,抛开造园传统不谈,中国大式木构的建筑传统似乎与西方在穹顶下书写的传统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并明显区别于日本。这是为什么在西方现代主义宗师们放弃了解体“盒子”的图谋那么多年之后,西泽立卫却仍孜孜不倦的在平面上延展着他的空间(图71),而《雅典宪章》的空间主张却从一开始就在中国水土不服。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傅熹年先生何以信手拈来的在中国佛寺的剖面中画出一个万神庙式的圆来(图7),以及王贵祥先生何以在东西方的建筑空间中酣畅的平行讨论上帝、佛与皇帝。 ↑图71:富弘美术馆模型 ↑图7:傅熹年的佛光寺内部空间分析 同样肇源自墙体承重的起点,比起西方拱顶在侧推力的逼迫下与支撑体系不断的水乳交融,中国抬梁式木构则因铺作层的壮大令梁架系统与支撑系统各自为政,从而呈现了逻辑更为清晰分明的结构美学——这是中国模式与西方的本质差异。那么,不止是“草原别墅”中屋顶与墙体在表现上的分离,密斯德国国家美术馆中柱顶与屋盖的清晰交割(图73),以及康的金贝尔美术馆拱顶与墙体间脱开的缝隙(图74),真的就全然得自西方自身的表现传统么? ↑图73:德国国家美术馆新馆柱顶交接 ↑图74:金贝尔美术馆 中国建筑师完全不必通过声嘶力竭的强调对日本的文化输出来间接论证自身传统对西方的影响,更不必太过在意赖特演讲中对《老子》思想的拙劣引用。除了近年来备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ntuoluoa.com/mtlhy/9912.html
- 上一篇文章: 曼陀羅,下載宇宙能量的通關密碼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